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
老漂族在子女家经历的带娃生活,家政服务13825404095重要却单调。在老漂自己眼中,带娃生活中暗含着几分宿命感,也有一些怨言。访谈中,经常听老漂讲一些简练而深刻的话,或表达他们对于自身命运的理解,或表达他们对自身角色的认知,或表达他们对当下生活状态的定位,或表达他们内心的矛盾和困惑。每个老漂语录里,都隐藏着老漂独特的人生体会。
老人就是不花钱的保姆
许多老漂认为自己是子女家的保姆。在不同的语境中,保姆这个词所表达的内涵或情感也有差异。
以前是带儿子,现在是带孙女嘛,就是帮助孩子们减轻负担。我们老两口带着孙女,照顾她上学、放学,做做饭,基本等于“保姆”。
老漂的工作内容类似于保姆的工作,准确地说,是住家保姆。住家保姆分为两类,一类是专门负责洗衣做饭、卫生清扫,另一类是专门负责带孩子。大部分老漂,把这两类工作都承担了,所以工作普遍比较繁重。老漂尤其是女性老漂,其日常工作就是带孩子、洗衣服、做饭、做卫生、帮忙取快递。孩子小的时候,需要更多照料,所以老漂时间比较紧张,工作内容安排得比较满,就像一个忙碌的保姆。
在老家,我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也轻松,很快就搞定了。现在过来做一大家子的饭很累,要考虑孙子爱吃什么、儿媳妇爱吃什么。不合胃口还要闹,不知道过来是养老,还是当保姆。(N9,男,77岁,丧偶)
我就像保姆一样,啥活都干,但又不自由,不像在自己家,想做啥做啥。(访谈案例编号C022)
两个案例中老漂说的保姆角色,也有不同所指。第一位老漂强调自己像保姆一样辛苦。虽然自己在家也要做饭,但是在儿子家做饭时,要考虑孙子和儿媳妇的口味,很费神。第二位老漂强调自己在子女家受拘束,不自由。许多老漂在子女家庭中分担家务内容多,但涉及家庭事务的重大决策时,子女却很少征求老人的意见,让老人感觉自己像个外人,没有参与家庭事务的权利。这进一步加剧了老漂生活中的边缘感,令老漂感叹自己只是干家务活的保姆。有学者在北京调研时同样发现:随迁老人普遍反映在家说话不算数。接受访谈时,超过一半的老漂自嘲为“保姆”“仆人”。下面这条微博更加生动地描述了老漂的保姆生活状态。
四妹妹到南方带孙子、带孙女去了,照顾儿子和儿媳妇的饮食起居。四妹妹每月工资,负责全家人的吃喝花销,儿子和儿媳妇从不给她一分钱。她每天既是仆人又是保姆,一天不得清闲。快到六十岁的人了,每昼夜为儿子一家人操劳。
每天,她成了机器人,买菜、做饭、带孩子,要忙到半夜才能入睡。南方的生活,睡得晚,起来得晚。每天早上,四妹妹出去买菜;上午十点,儿媳妇带着两个孩子才起床,四妹妹给他们做好饭菜,吃完早饭,是十一点;中午,儿媳妇带着孩子睡觉;下午四点,才吃中午饭,吃完饭,儿媳妇带着孙子出去玩,四妹妹在家看护孙女;晚上六点半,儿媳妇带着孙子才回来,此时四妹妹才给他们做饭,儿媳妇和孩子吃晚饭的时间是晚上八点多;吃完饭,她们给两个孩子洗澡,四妹妹开始给小孩子洗衣服、洗碗筷、擦地等;四妹妹休息的时候,已经是半夜十一点多了。
此时,她会给我发微信,告诉我一些事情。四妹妹从退休起就开始为儿子家操劳,每天团团转地为儿子一家四口人忙碌着,如今,大孙子才二十个月,小孙女才四个月。过两个月,儿媳妇还要上班,儿子到很远的地方工作,那时,两个孩子都要靠她去照顾,大孙子每天哭闹,真是有劳她了。(微博用户凌**发表于2018年9月6日)
上面这条微博是一位老人对其四妹生活的描述,用三个词概括了老漂的角色,分别是仆人、保姆和机器人。其中,“保姆”这个词主要描述了老漂的工作内容,涉及带孩子、买菜、做饭、洗碗筷、洗衣服、擦地等;“机器人”这个词主要描述了老人的工作节奏和工作强度,即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;“仆人”这个词侧面反映了其家庭地位。大多数老漂虽然角色很重要,但是在子女家缺少话语权。在许多事情上,子女缺乏对老人的尊重。

带娃生活把老人逼成了全能选手
老漂群体中还流行“带薪保姆”的说法。所谓带薪保姆,特指那些有退休金的老漂。他们不仅免费为子女承担家务,还用自己的退休金补贴子女家庭生活,为子女提供经济和劳动双重支持。
感觉现在养老金已经变成“养小金”,像有些老人都已经没有上班,拿的养老金还要掏出来给子女养小孩。就是女方没出去上班带小孩,男方工资也才五六千,有贷款要还,男方妈妈把养老金当工资发给儿媳妇在家带孩子。(微博用户普**发表于2023年6月28日)
一些农村老漂虽然没有退休金,但因为儿子、儿媳妇在城市生活经济压力大,所以进城后也主动贴补儿子。家住陕西咸阳农村的金女士,在西安帮儿子带孙子八年,每个月还要自己出1.000元,用于买菜、给孙子买零食。按金女士自己的说法,虽然儿子、儿媳妇也给零花钱,但老人自己手上有钱,还是感觉好很多,主要是不受气!在金女士及其子女的老漂家庭中,1.000元发挥的作用,不只是经济支持,还是关系润滑剂。也正因为如此,金女士的丈夫每个月还要在农村打零工挣钱。他和老伴分工合作,以不同的方式支持儿子一家的在城生活。(访谈案例编号C066)
带孩子是一份工作
都江堰的景女士在事业单位工作,目前孩子还不到1岁,由婆婆帮忙照看。景女士的老公在一家软件公司工作,频繁出差,十来天才能回来一次。景女士的丈夫出差回来后,也尽可能主动带孩子,但是和景女士一样,因为带孩子时间太少,方法技能不熟练。孩子和父母感情不深,更喜欢让奶奶抱着。这就让景女士和老公有些尴尬,很想照料孩子,但是不得要领,看着孩子哭闹,不知所措,最终还是让老人抱着才行。当老人看到儿子、儿媳妇哄不好孩子的时候,自己也会有点无奈。(访谈案例编号C023)
景女士的婆婆之前在老家给大儿子带过两个小孩,现在带的是第三个孩子。景女士的婆婆对笔者说:“给儿子带小孩,是一份工作。开心也是干,不开心也是干,还不如开开心心干!”(访谈案例编号C024)
她说这句话的时候,正抱着孩子。在儿媳妇看来,婆婆之所以将带孩子理解为工作,主要有两个意思:第一,这是老人的职责所在。奶奶带孙子,天经地义,责无旁贷,必须尽职尽责。第二,这是老人自我排解负面情绪的一种方式。给儿媳妇带孩子,难免会发生矛盾。不开心的时候,也不要过于在意,只是一份工作而已。其实,还可以把这句话放在老人这些年带孩子的经历中来理解。毕竟之前已经带过2个孩子了,相当于同样的程序再走一遍,已经非常熟练。带孩子是近些年自己的一份稳定的正式工作,一直在做,只是没有工资而已。
景女士每天工作忙碌,早上出去、晚上回来,顾不上孩子。其实,婆婆和她一样,也在做着工作—“带孩子”,在家上班,整天忙碌,关键是没有休假。西安的姜先生认为:“自己下班回来,必须带孩子,让老人休息,毕竟老人在家上了一天班了。”(访谈案例编号C010)
西安的牛先生也认为带孩子是一份工作,只是他赋予这份工作更多内容,心态上也更加积极。在他看来,带孩子不是一份普通的工作。这是一份全职工作,各方面都要照顾好。要注意孩子的安全,这是最基本的。在此基础上,要注重孩子饮食、营养搭配;要注重孩子智力开发,让孩子接收更多信息,给她读唐诗,带她逛公园、坐公交车见世面。牛先生还认真学习了育儿畅销书《好妈妈胜过好老师》,参照其中的理念带孩子。(访谈案例编号C001)相比西安的牛先生,来自海南、漂在广州的李女士则展现出更强的学习能力。
为了带好妞妞,要学的东西更多了。李姨每天边做家务边听节目、付费课程,包括幼儿教育、音乐讲座、听书等。“只有自己的知识面广了、眼界宽了,才能把孩子带得更好。”如今,李姨还经常研究做饭,在网上找视频教学,摸索出营养又符合妞妞口味的美食。妞妞喜欢吃汁多的饭菜,李姨经常做肉末加胡萝卜丁,搭配各种蔬菜。
牛先生和李女士可谓典型的学习型老漂,个人能力强,活力充沛,其对孙辈的抚育内容,已经远远超出了“带孩子”的范畴,成为一种专门性的育儿工作,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。按牛先生的理念,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“工作态度”,即把带孩子当成一个“工作”,认真去做,而不能像以前那样主要关注孩子的温饱。不容否认,像牛先生和李女士这样带孩子的老漂并不多,他们在老漂群体中只占极小比例。持这种“工作态度”的老漂,更受子女的欢迎,毕竟在育儿理念方面,两代人处于一个频道,更容易交流沟通。
有些老人自我调侃,自己刚退休,还没来得及休息,就又上岗了,给儿子、儿媳妇带孩子。有的家庭是男方父母带半年孩子,女方父母再带半年。这相当于轮岗模式。那些孩子已经上小学或上初中的家庭,老漂基本完成任务,返回老家,称自己下岗了。
带孩子就是卡时间和磨时光
访谈中,男性老漂单独带孩子的情况并不多见。西安老漂翟先生的情况比较特殊。妻子走得早,留下2个女儿,当时大女儿3岁,小女儿1岁。翟先生自己把2个女儿拉扯大,所以比大多数男性老漂有带孩子经验。目前,翟先生在西安给小女儿带孩子,租住在一室一厅的房子里。客厅里放了一张床,翟先生睡在这里。床对面是电视机,最近坏了。看不成电视,翟先生说自己更加无聊了。(访谈案例编号C013)
聊起带孩子的体会,翟先生用了两个词—卡时间和磨时光。
所谓卡时间,即带孩子一定要摸清孩子相关活动的大体规律,然后在适当的时间节点做适当的事。比如孩子小的时候,一定要卡好把尿的时间,此外,还要把握喂奶、午睡的规律。在翟先生看来,只要卡好时间,带孩子就很简单。
所谓磨时光,即带孩子过程中一种特殊的时间体验。翟先生说:每天有很多工作,除了卡准孩子作息规律,还要洗衣服、做饭、收拾房间,这些事一件件做完,一天的时间也就磨完了。今天的时间磨完了,明天继续磨。每天的生活具有高度的重复性。
外孙女上幼儿园后,翟先生每天早上送去、晚上接回来,白天就有大把时间让自己消磨。如果说孩子小的时候可以推婴儿车出去溜达或陪着孩子游戏,时间磨得还有些趣味,过得比较快,那么现在孩子上幼儿园了,自己一个人的时间就更加难磨了。
翟先生干完家里的活,就下楼转转,到广场上看看热闹,看别人下象棋。他只能看棋,没人和自己下。在楼下溜达,不想和人搭讪。他认为城中村人员复杂,不安全。和楼下的一个男的说过几次话,但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租客还是房东。翟先生从没细问过这个男的来历,在他看来,知道也没有意义。在楼下转久了,感觉也没啥意思,就回到家里。电视坏了,只能自己摆扑克。时不时看看表,卡时间去幼儿园接外孙女。
听翟先生讲述他的老漂生活,有一种特殊的感觉,那就是单调中夹杂着几分消沉。这既和他多年一个人独自生活的经历有关,也和他男性老漂的身份有关。大部分女性老漂习惯了在家务事中消磨时光,也能在楼下和其他女性老漂聊聊家务事,时间不知不觉就磨过去了。男性老漂的时间体验有其特殊性,脱离了既有的熟人社会,在新的生活空间中没有新相识、新兴趣,日子就很难过,就涉及消磨时光的现实问题。
翟先生案例的另一个启示意义在于,老漂群体在新生活模式和环境中的时间感,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话题。因为孩子成长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,抚育活动具有高度的日常性和重复性,所以老漂生活就比较单调,会影响其心理状态。这一点,应该被老漂的子女所关注和理解。

老人带娃成了小区里的常见景象
老漂生活像坐牢
有老人用“坐牢”来形容自己的老漂生活。这绝不是说儿女限制了老人的人身自由,而是老人的一种主观感受。
从工作状态角度看,老漂不自由:每天带孩子,还要忙家务,没有休息日,连续工作。特别是孩子小、孩子妈妈又特别忙的时候,老人就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自由,都是被安排的。来自山西、漂在北京的一位老人这样介绍自己的老漂生活:
早上6点起床做饭,饭后老伴儿送老大上学,我送老二去幼儿园,回来的路上买点菜,上午打扫屋子,午饭后洗洗刷刷再准备上晚饭食材。下午不到三点,老伴儿就要动身去接老大;儿子、儿媳妇下班晚,放学后再送他去英语、绘画等各种补习班。
这位老人所描述的,是许多老漂的日常。老漂们将自己的生活状态概括为三点一线,即每天在“家/学校/菜市场”之间转悠。有老漂认为自己的生活被孙辈彻底套牢了。也有人将老漂的生活概括为一个人画圈的生活:
从早上5点多起床开始,买菜、做饭、看孩子……老人的生活似乎一直画着一个圈。没有其他娱乐,老人就早早睡觉,第二天又是一个新的圆圈。
从生活空间角度看,许多老人住惯了农村宽敞的平房,喜欢宽敞的院子,所以住在楼房里感觉特别憋屈,厨房、客厅、卧室都不如老家宽敞,空间狭小,不自由。有老漂则认为自己过的“完全是关在家里面”的生活。
我觉得在这边的日子,虽然说不上不顺心吧,但是确实没有在老家的生活过得舒服啊。在这边的话,我感觉我自己越来越少走出家门了。以前在老家的时候还有个跳舞的爱好,到这边好像就完全是关在家里面了。(访谈案例编号X013)
在老家找人盖的两层楼,前两年又重新找人搭了两间厨房,家里人多,房间也多,我家是三间的(宅基)地,宽敞得很。院子大,俺俩在院子里还种点菜,想吃随时就摘了,出门也方便,门一锁说走就走了。到这边之后,我小儿子家在16楼,上下楼都要坐电梯,不方便。关键是房子小,走不开人,没有办法,哪有那么多钱(买大房子呢)呢?(访谈案例编号W008)
有些子女考虑到户外空气质量不好,怕影响孩子健康,于是限制老人到户外带娃,这同样会加剧老人的压抑感,感觉自己被囚禁了。
60岁的杨淑琴从赣榆来南京已有3年,儿子常出差,难得在家。儿媳妇总说外面空气污染重,不让她带孙子下楼玩。“小孩子总闷家里哪行呢?我就趁着她上班时偷偷带出来。”有一次,她带孙子在小区广场玩,正巧被儿媳妇撞到,儿媳妇当众责怪她:“孩子要是呼吸脏空气生病,你负责?”杨淑琴气得头晕,回家就给儿子打电话:“我来带孙子,不是坐牢的!”儿子赶紧回家“调停”,结果还得服从儿媳妇:只能带孙子在阳台上玩。至今她还后悔当时冲动,让儿子两头为难。
除了空间和生活状态的不自由,还有一些老人感觉自己在履行父母责任时有一种被压迫感。“脱不了壳”,这是西安敖女士的父亲对自己生活状态的概括。他所说的“壳”,既可以指抽象的代际责任,也可以指目前的家庭结构。几年来,敖女士的父母不仅帮忙带孩子,还帮忙装修,大小事务都跟着操心。老人感到肩上担子很重。儿女已经长大,但老人还是不放心。(访谈案例编号C048)
老人身上的“壳”,对女儿来说,就是一种巨大的保护。老人说“脱不了壳”,意思是想摆脱,但无法摆脱。无法突破的结构,给人一种持续性的限制。
孩子们回家后,王燕的母亲又常常感到很失落:“他们回来后,要么看电视、玩手机、逗孩子,要么还要忙工作。我理解,他们白天累了一天,不想说话很正常,但这样的生活确实令人感到煎熬,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被判了‘有期徒刑’,不知道什么时候能‘刑满’回家。”
一些老漂用“有期徒刑”或“无期徒刑”来描述自己当前的生活状态。如果是“有期徒刑”,那就是等孩子大了,才可以真正摆脱这种每天带孩子的状态。如果是“无期徒刑”,那就意味着要一直带孩子,好像没有尽头,遥遥无期。如果子女又生了二孩,那就相当于加刑了。
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浙江籍大哥说,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漂,不但漂在杭州,负责接送孙子上学,而且曾漂洋过海到过美国。他说,在美国的那半年,好像是把半年生命舍给女儿了。虽说也读过点英文,但只限文字。“读、写、听、说”。“读、写”尚且不精,“听、说”全然不会,几乎就是哑巴英语,不会与人交流。(案例信息来自《杭州老漂日记》,2017年11月3日)
案例中的老漂曾到美国给女儿带孩子。跨国老漂面临着更大的社会适应难度,特别是在语言交流方面。这位老漂说“把半年生命舍给女儿了”,将半年老漂经历描述为“舍命”,足见那半年生活的艰难程度,仿佛在异国被囚禁。
陕西合阳农村的一位老人,也用“坐牢”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在儿子家的生活状态,最主要的感受就是受拘束,不像在自己家那样自在轻松。老人爱抽烟,但是儿媳妇多次强调不能抽烟。自己烟瘾犯了,也只能到楼下抽。老人喜欢看电视,但是也怕吵到孩子休息。更不习惯的是,自己和老伴早上醒得早,但是“醒了却不能起”,害怕吵醒儿子和儿媳妇。老人说,早上憋在卧室里那种感觉,就像在坐牢一样。(访谈案例编号C063)
此处老人说的“坐牢”,更多涉及的是一种精神心理状态。有些男性老漂在儿子家时,即便儿子、儿媳妇不当面指出老人抽烟等生活习惯问题,老人自己还是觉得浑身不自在。陕西咸阳金女士的丈夫说,儿子、儿媳妇虽然不说我,但自己作为老人也要自觉。正是这种自觉意识,让老人在子女家感觉放不开,有一种无形的约束。(访谈案例编号C066)
许多农村男性老漂正是因为不习惯在城生活的不自由状态,才不愿意(甚至抵触)跟随老伴一起到儿女家生活,即便什么都不干,也待着不自在,无所适从,或多或少精神紧张。这主要是因为,老漂家庭普遍以年轻人和孩子为中心建立生活规则,对老人无形中产生束缚。相比较而言,来自城市的男性老漂,经过多年城市生活的洗礼,在生活习惯方面与儿女一致性强,所以拘束感会相对少一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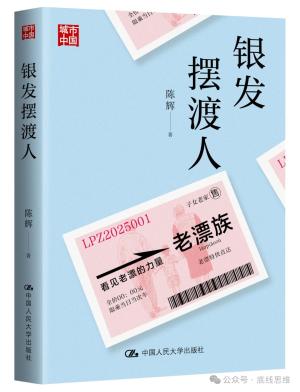
本文摘自《银发摆渡人》,略有删节,陈辉 著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
继续滑动看下一个轻触阅读原文

底线思维向上滑动看下一个
底线思维赞分享推荐 写留言 ,选择留言身份
原标题:《从“不花钱的保姆”到“生活像坐牢”,老漂有多苦闷?》